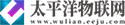记得读高中时语文试卷上有这样一道题,现在估计不再会这样出题了吧:以下哪位作家被称为“世界短篇小说之王”?A.契诃夫 B.莫泊桑 C.欧·亨利。“正确答案”是B。
这个题目显然有失严谨,“世界短篇小说之王”据说是法朗士给莫泊桑的称号。当然也会有很多人认为这个头衔更应当属于契诃夫(或欧·亨利),尽管他们的创作手法大相径庭。契诃夫本人却对莫泊桑非常重视,契诃夫认为写作是一件难事,因为毕竟莫泊桑的才华已经将写作提到那么高的高度了——这意味着莫泊桑是他的一把“标尺”。
虽然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都对莫泊桑不吝赞美之词(对于这两位来说的确不多见),但对他们而言,长篇小说、大部头巨著才是孜孜以求的目标——对于19世纪作家来说,长篇小说才是“珠穆朗玛峰”,莫泊桑显然也有此雄心壮志。但《一生》《漂亮朋友》等长篇显然不如其短篇令人印象更深刻。对于短篇小说来说,机巧、突转、“出乎意料又合乎情理”都很重要。但是俗话说“巧不如恰”,莫泊桑的短篇小说总能给人恰到好处感,总是在最恰当的时候结尾,余韵袅袅。他的长篇就难以给人这样的回味。
 (资料图)
(资料图)
莫泊桑的激情
契诃夫的“无聊”
契诃夫同样以短篇小说著称,他和莫泊桑总是被放在一起比较:这二位在男作家中都算得上相貌堂堂,连不同风格的胡须都成为被反复议论的对象,甚至他们都在人生最好的年龄去世。但是他们的小说却如此不同。契诃夫是写“无聊”的大师,无聊!这正是现代人的通病,即人生的虚无感,但是怎么办呢?专家们说,契诃夫不告诉我们“怎么办”。可是,他的主人公说,要忍耐,须耐烦,他的主人公不是浪漫主义文学中的英雄,他们要么在无聊中无聊下去,彻底成为无聊本身(《姚内奇》);要么在无聊的生活中找到自己生活意义的完整,哪怕在别人看来是平庸的(《海鸥》);要么他(她)本来就是自足的,比如,《宝贝儿》不正是和福楼拜的《一颗质朴的心》有异曲同工之妙吗?
作为福楼拜的好学生,莫泊桑的主人公不能忍受“无聊”。福楼拜说,“包法利夫人就是我”,爱玛·包法利并没有什么原罪一类的过错,她只是需要用想象力来装点一下无聊的人生。莫泊桑的小说也写人生的虚无,梦想的破碎,但是他的文字里总是有一种激情的涌动,这是带有肉欲色彩的涌动。“羊脂球”是非常形象的、肉感的,她不是“微胖女孩”,而是“大码女孩”。曾经收入高中语文教材的《我的叔叔于勒》多年后最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其中对吮吸牡蛎的描写。牡蛎这种食物和吮吸的动作都是有肉体意味的。莫泊桑似乎也写主人公历经艰辛后得到了生活的感悟,但是,《项链》的最后一句是什么?那个女主人公为之付出了青春的钻石项链是假的。这不是在写人生的荒诞又是什么?这与《一颗质朴的心》是完全不同的。
当我们回顾莫泊桑的时候会发现,他虽然和当时的大作家们一样揭示了社会的转型,批判资本给人带来的“异化”,也体现在人的爱情观、婚姻观的“异化”上,但他笔下的人物总是保留着真正的爱欲能力。爱欲,是莫泊桑试图用来抵御荒诞感的东西,尽管他知道这终究是不会成功的。他笔下的爱情也没有“成功”的,但是那种精神和肉体的欢愉正是生命的一种证明,是带有酒神意味的——他自己的早逝也与此密切相关——这种本能的感受在今天却是尤为珍贵的,因为现代社会是一个各种科学“还原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连爱欲也已经被还原为一种“亲密关系”。这就意味着它完全可以折算成各种数据来算计,但爱欲恰恰是不能这么算计的。今年是莫泊桑离世130周年。看到这个数字,仔细想来,其实并不算特别遥远,他去世仅两年后,电影就在法国诞生了。假如他能再多活几年,会不会用这种新的媒介进行爱欲书写?极有可能。
雷诺阿调亮了
莫泊桑作品的“色度”
不过,电影人可不会放过他的小说,无论从体量还是情节看,他的短篇小说看起来都比较适于银幕化。但是实际上大作家的“大作”银幕化后往往难以跻身一流的电影行列,反而有些不是那么出名的篇章到了大银幕上更令人回味无穷。这是由电影媒介本身的特点决定的,没有一个艺术家能够完整“再现”另一个艺术家的艺术思维,更何况是用完全不同的另一种语言呢?但是也有这样的情况,有的艺术家可以在小说中发现能够产生一部影像的材料,这样就有可能产生火花,留下影史杰作。
法国电影大师让·雷诺阿的旷世杰作《游戏规则》近期在上海艺术电影联盟十周年“法国电影大师展”上放映,这也是这部伟大影片的高清修复版首次登陆中国大银幕。作为印象派大画家皮埃尔-奥古斯特·雷诺阿的儿子,让·雷诺阿是在法国文学艺术核心圈层里长大的,他本人和左拉等作家关系也很好。
《游戏规则》是雷诺阿自己编剧的,导演用丝滑的场景调度完成了情节的层层推进、人物繁复关系的交代、阶级议题的表达,无可辩驳地证明了电影语言丝毫不亚于文字语言的艺术表现力。电影首先是艺术,是智慧,而不是科技加狠活。
这个故事隐约有着莫泊桑的影子:在爱欲关系中最付出、最投入的反而成了唯一的牺牲品,在这个以自私自利为底色的、密不透风的社会关系中,他成了不遵守“游戏规则”的那个人。但是这个荒诞、幻灭感的主题并非要让人恐惧爱情婚姻,而是相反的,即没有了爱,这个轻佻的、遵守游戏规则的世界是更令人难以忍受的。
雷诺阿的《乡间一日》很少被重视,但其实这是一部极为杰出的电影。它改编自莫泊桑的短篇小说《郊游》。值得一提的是,托尔斯泰严厉批评过这个小说,因为他认为作者在其中表现出来的道德感是暧昧的。而雷诺阿改编这个小说的动机是他认为破灭的爱情,庸碌的一生,莫泊桑用几页纸就写出了一部大部头小说的内容,他就是要将这样的精华搬上银幕。当然另一个理由或许是,莫泊桑正是他父亲的故交。除此之外,这也是雷诺阿的一次试验,他想挑战观众对短片的接受程度。不过这部作品实际上没有最终完成,在二战后根据他原来的创作意图,才剪辑出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版本。但从40分钟的体量以及完成度来看,很大程度上还原了原貌。
故事讲巴黎的杂货店老板娘过生日,老板杜富安排了一家人去乡间郊游:杜富的母亲、老板娘、女儿三代女性,老板和未来的女婿两个男人。孰料两个在此的水手从窗户里看到了荡秋千的美貌的母女二人,他们临时决定来一场勾引/艳遇。他们用计将杜富先生和他的准女婿支开,各自对杜富夫人、杜富小姐施展手段,并各自顺利得手。杜富先生和女婿对此毫不知情,于是一家人高高兴兴地回去了。
如果故事只写到这里,那不过就是19世纪常见的一种写偷情和出轨的文学,只不过是人生一段小插曲的描述。对于故事里的杜富夫人来说是这样的,杜富先生显然粗俗、庸常、市侩气,和这个健壮俊俏小伙子的露水之欢,只是她生活的调剂,也就是说,是一种“游戏规则”,认真你就输了。但是杜富小姐与另一个年轻人之间却产生了强烈而真实的爱情。我们不能将其简单粗暴地理解为“恋爱脑”:她回家后就结了婚,正是嫁给了那个不解风情的、滑稽的、接管她父亲店铺的年轻人。此后的一年间,杜富小姐和水手这两个年轻人无时无刻不想着彼此,这种对爱的确认感越来越强烈——尽管后来发现爱情实际上是两人见不到彼此的情况下发生的。然而,一切晚矣,一年后他们再相见,小伙子告诉杜富小姐,一年来他每周都来这里,每晚都在回忆。两人相看泪眼,就此结束。这也是最动人的地方。“这一年”作者没有写一个字,却仿佛又写了千言万语。契诃夫的小说《带小狗的女人》的结尾仿佛可以为此做个注脚。这两个人心里明白:离结束还远着呢,那最复杂、最困难的道路现在才刚开始。
雷诺阿将这部影片献给他父亲那一代人。和后来的《游戏规则》不同,这部影片完全使用了自然外景,这当然是他想致敬的印象派美术本质决定的,印象主义,就是看待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新的视角。但是就当时的摄影技术来说,这是相当冒险的。虽然今天的后期软件可以修成斑驳的油画效果,但这种古早级别的摄影却呈现出意想不到的清新自然感。影片中树荫的斑驳没有任何“后期”感。导演的构图无疑来自雷诺阿的《青蛙池塘》《秋千》等油画,甚至可以说大部分我们看到的镜头都能与印象派绘画一一印证。例如,杜富小姐荡秋千时,穿的服装都与画中一样,简直就是从雷诺阿的画中荡漾出来一般。导演赋予了原著小说里没有的视角,杜富小姐徜徉在自然中,听着夜莺的歌声,观察毛毛虫,在懵懂的初吻中遭遇突如其来的滂沱大雨,都直观地建立起一个和自然一体的女性形象。雷诺阿在莫泊桑的基础上调亮了好几个“色度”,但是,赋予原著以轻快明亮的气息就是“肤浅化”吗?未必。这部影片的“后劲”很大,很有几分费穆《小城之春》的韵味。
《欢愉》对莫泊桑的“美化”
德裔法语电影大师马克斯·奥菲尔斯的《欢愉》也对莫泊桑原著进行了“美化”。电影毕竟是电影,电影面对的观众毕竟不是文字读者。莫泊桑说“现实主义”的时候,他指的是艺术要高于生活本身,他在诉诸文字的时候,需要做到冷静、克制地表达自己的情感。是的,莫泊桑是一个情感动物……但是你会发现他刻意地抵制写“美”,或许因为“美”对他是一种致命诱惑。但电影不同,总得吸引观众吧?不过,这归根到底取决于电影作者的立场。当奥菲尔斯拍《欢愉》的时候,他当然是对莫泊桑进行了取舍的。
这部影片由莫泊桑的三个短篇小说组成,都与欢愉(pleasure)有关,但这三个故事的比重是不同的:第一个和第三个故事都只有不到20分钟,第二个故事却有一个多小时时长。欢愉,都与爱欲有关。第一个故事讲的是欢愉与爱慕:曾经的舞场高手如今垂垂老矣,他因为要维持着自己依然受女人爱慕的幻想,给自己做了一个年轻的面具,他戴着蜡像一般的面具依旧夜夜跳到很晚,直到心脏病发作倒在舞场。第三个故事讲的是欢愉和死亡,是一个“爱到尽头覆水难收”的故事:画家爱上了自己的模特儿,他们如胶似漆,寸步难离,爱渐渐成了一种纠缠和捆绑。画家几次欲离开,模特儿次次自残,终于致残,这段虐恋终于转化成了一种道德义务,他们厮守终生。
开头和结尾的故事显然是为了烘托第二个故事,即欢愉和“单纯”。但是“单纯”的主人公却有着特别的身份。故事改编自莫泊桑的短篇小说《泰利埃公馆》。故事发生在法国的一个小城费康,“太太”开了一个“公馆”,里面有五个女郎,她们像是女招待,但其实都是干“那个”的,主要服务小城各阶层的人士。但是“太太”给她们一种尊严,不许客人们诋毁她们,在公共场合也要称呼她们“夫人”。某日,太太接到诺曼底乡下弟弟的来信,外甥女到了初领圣体的年龄(12岁)。作为孩子的教母,她要到场参加,便索性带着五个女子一起坐上了火车。这里,我们看到19世纪中叶,火车已经成为城乡之间的交通工具,现代城市文明对古老宁静乡村的腐化已经成为时髦话题。但莫泊桑没有这样写。在他的笔下,诺曼底乡下的农民保持着淳朴的精神,他们并不另眼相待这些奇装异服的“夫人”,对他们进入教堂参加仪式也毫无异议。
奇特的一幕就在这里发生。“初领圣体”是天主教的仪式,通常都很郑重,它意味着对救赎意义的理解。在这个时刻,其中最出挑的罗莎夫人被这种气氛感召,流下了激动的泪水。而她的眼泪仿佛会传染,从轻声抽泣到泪流满面,渐渐地教堂里所有的人都跟着流泪,这场礼仪真正成了“净化/升华”的一个特殊时刻,而且这是由一个特殊身份的女人引起的,她与“抹大拉的玛利亚”形成了一种奇妙的呼应,并因此还赢得了有淳朴信仰的乡民的尊敬。
奥菲尔斯显然抓住了莫泊桑这篇小说最重要的东西,虽然莫泊桑在小说中把这些女子写得很难看、很丑,而且她们最后还是得回到城里去继续她们的营生,但是最重要的是,小说中的这段描写让一切都发生了改变。一个漫不经心的读者体会不到这一点,但奥菲尔斯将其变成了自己的一种独特的个人印记:他起用法国电影第一古典美人达尼埃·达利约扮演罗莎夫人。由于她的演绎,也由于她本人的坎坷命运,救赎的意味更为明显。导演将这一段拍得极具感染力,甚至可以说很催泪。这也让《欢愉》和《伯爵夫人的耳环》《一个陌生女子的来信》一样,呈现出导演本人的、迥异于文学原著的“作者风格”。
不止一位电影大师对莫泊桑“下手”。西班牙电影大师布努埃尔被低估的《没有爱的女人》即改编自莫泊桑的短篇小说《皮埃尔和让》,这也是一部有待重新评价的作品。在爱欲的激情和四平八稳的关系中选择安稳,难道真的就会带来心灵的安宁吗?显然未必。布努埃尔把握住了莫泊桑小说的主旨。而《羊脂球》除了在法国被多次搬上银幕外,苏联电影大师罗姆的1934年版也可圈可点;而美国大导演约翰·福特的经典名作《关山飞渡》更是令人意想不到地将《羊脂球》的情节嵌入了美国西部片中。有意思的是,费穆生前监制的最后一部影片《花姑娘》(1951,朱石麟导演)也改编自《羊脂球》。以“余韵”见长的费穆或许也曾经从莫泊桑的艺术手法那里“偷师”。如果我们再大胆一点,甚至会发现,小津安二郎的《东京物语》虽然情节和故事与《羊脂球》完全不同,可是它的叙述方式、节奏、平静叙述下跌宕起伏的内心活动,对“势利”社会环境下人性的洞察,都与莫泊桑何其相似。这两部作品呈现出一种共同的诗学质感。
小津说,电影以余味定输赢——对小津顶礼膜拜的法国新浪潮一代导演们,不知是否也在其中感受到了莫泊桑的“余味”?如果我们觉得今天的电影鲜少有值得回味的,又或是电影里的爱情总有一股工业糖精的味道,不如回到莫泊桑这里看看,如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