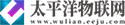《傅璇琮文集》,中华书局2023年4月出版
 【资料图】
【资料图】
傅璇琮先生
“纪念傅璇琮先生90诞辰暨《傅璇琮文集》发布会”活动现场首先要向清华人文学院、刘石教授以及我的老同事中华书局学术中心的编校同仁,表示我个人由衷的敬意,感谢大家为傅先生《文集》付出的辛劳。《文集》是我动议的,也参加了前期的体例商讨,刘石教授慨然支持并承担起组织落实工作,使《文集》顺利启动。这时已经是2021年10月,年底我就卸任了,一直到今年2月国林发我会议邀请,上周拿到样书,非常惊叹《文集》编校工作的高效和《文集》规模之巨大、成书之典重精美。
本周我用三个日夜,翻阅了二十四册《文集》,主要读纯学术文章以外的篇章,感触很多。傅先生1992年为《文史知识》写了一篇《读〈启功丛稿〉一得》,说:“过了10年,正如白居易所说,年岁渐长,阅事渐多,近日重读这部著作,产生出一种从未有过的亲切感,享受到一种在学识追求上得到极大满足的愉悦。”(《驼草集》937页)读到这里,我想,傅先生说出了我读《文集》的最准确的感受。
1988年,作者(左一)与傅璇琮先生(右二)在晋祠合影
1991年,作者(右二)与傅璇琮先生(正中)在北京十渡合影
1998年,作者(右二)与傅璇琮先生(正中)在贵阳合影在2016年9月唐代文学学会成都年会为傅先生举行的追思会,我讲了对傅先生的两点认识——一是“丁酉之祸”对傅先生的影响;二是编辑职业对傅先生学术形成的影响力。这次重读,加深了对傅先生的理解。简单讲感触最深的两点。
一、傅先生柔弱、谦和的外表下有强毅、强大的品格和对学术追求的强烈信念。
傅先生《文集》中多处回忆被打成“右派”,到商务、中华工作初期的情况,在那么重的政治压力下,“我这个人毕竟是个书生,从50年代起,不管环境如何,总是抓时间读书作文”。1973年从干校回京后,“虽已是文革后期,但政治运动仍很频繁,且当时还没有个人著作出版的希望,但我不管这一切,日夜躲在书室中,读书写文”。“我们这样的读书人或学者,不必有什么需求,更不必有什么做官、致富的奢望。如果有什么需求,那就应该是,自己所做的要在时间历程上站得住,在学术行程中得到认可”(《唐代诗人丛考》2003版前记)。这次读到《驼草集》卷首傅文青写的“弁言”,说到傅先生听到自己被划为“右派”后的反应,“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三天,看了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然后就出来了”,“书中的安德列战场受伤后,躺在俄罗斯广袤无垠的土地上,看到的太阳是黑色的,他的心沉到了海底,但他看到了俄罗斯的年轻人勇敢前行坚强不屈时,太阳又是红色的了,给了他希望”。现在我们很难想象关在房间里的三天,傅先生都经历了怎样的思想挣扎,但我们能够清楚看到那一代人独特的信仰。傅先生还不止一次引用雨果的话:“艺术就是一种勇气!”引用巴尔扎克的话:“我也许能够写出一部史学家们忘记写的历史,即风俗史!”一再引用陈寅恪为杨树达所撰序里的话:“寂寞勤苦,逾三十年,不少间辍,持短笔,照孤灯”,“非彼假手功名,因得表见者,肥瘠荣悴,固不相同,而孰难孰易,孰得孰失,天下后世当有能辨之者”(《近代学术之源泉——读〈嘉定钱大昕集〉》,《驼草集》1510页)。理解傅先生的思想境界,才能理解他周末一个冷馒头对付,日复一日在图书馆查检抄录群书,完成百万字的黄庭坚与江西诗派、杨万里范成大两部资料书,才能理解在云梦楚泽就开始《唐代诗人丛考》的准备,在晚年仍然开启唐代翰林学士的考证,才能理解一直到晚年傅先生都保持着写作的冲动,保持着借助各种形式的写作发言来表达自己对学术的关切。我现在也过了花甲之年,看到这一点,尤为感佩。
傅璇琮先生完成的《杨万里范成大资料汇编》《黄庭坚和江西诗派卷》两部资料书
傅璇琮先生所著《唐代诗人丛考》及主编的《唐才子传校笺》傅先生虽然讷于言说,但笔下的文字洋溢着哲思和诗意,最为大家熟悉称道的是《唐代科举与文学》序言描叙从兰州到敦煌一段路的见闻与感想:车过河西走廊,在晨曦中远望嘉峪关的雄姿,一种深沉、博大的历史感使我陷于沉思之中,我似乎朦胧地感觉到我们伟大民族的根应该就在这片土地上。
在通往敦煌的路上,四周是一片沙碛,灼热的阳光直射于沙石上,使人眼也睁不开来。但就在一大片沙砾中间,竟生长着一株株直径仅有几厘米的小草,虽然矮小,却顽强地生长着,经历了大风、酷热、严寒以及沙漠上可怕的干旱。这也许就是生命的奇迹,同时也象征着一个古老民族的历史道路吧。
……
其实,《文集》中类似这样的文字还有很多,读来身临其境,精神可感。在安阳农村搞“四清”时,看到揭批《新编唐诗三百首》的报章:
安阳是殷墟的旧地,甲骨文是我们文明的老祖宗,我倚伏于中原大地上一家农舍昏微的灯光下,面对这篇檄文,真感慨于我们古老的历史传统中一种可怕阴森的东西。(《热中求冷》,《驼草集》1334页)
在咸宁向阳湖干校,最后两年,人走的差不多了,劳动战地变成了休闲场所,晚饭后有时找萧乾、楼适宜夷等先生聊天,后即转入屋内,点起煤油灯看书——先期回京的杨伯峻先生寄来的《三国志》、范注《文心雕龙》:
咸宁地处楚泽,广漠的平野常见大湖返照落日的奇彩。晚间我遥望窗外,月光下的远山平湖,仿佛看到这屈子行吟的故土总有一些先行者上下求索而悲苦憔悴的影子。这时心也就渐渐平下来,埋首于眼前友人从远地寄来的旧书中。(同上)
傅先生在谈朱东润先生史传文学时说:“读朱先生的著作,总会感到一种人格的力量,又能受到做学问的一种极难得的启示和陶镕”,“既要有理性的思索,又要有情感的倾注,这样才能使传统的研究蕴含一种‘秋冬之际,山阴道上’的眷恋情怀,又能有一种‘仲春令月,时和气情’的舒朗气息”(《理性的思索和情感和倾注》,《驼草集》1293页)。用傅先生这段话,来理解他那些富有历史感的美文,非常切合。与其说是诗意美文,毋宁说那就是傅先生人格的外化。
二、如何认识作为出版家的傅璇琮先生?
匆匆读过十册《驼草集》,另一个印象深刻的方面,是作为出版家的傅先生,他的焦虑和努力,跃然纸上。过去我未曾着意,读后有一些新的理解。
在我们经历的近四十年出版历程中,出书难、出书慢和经济效益考量,可以说贯穿始终,非亲历者不能深知。傅先生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前后二十年时间担任中华书局副总编辑、总编辑,也是他的最大的困扰。
《学术漫录》是1980年代以后深受读者喜爱的不定期集刊,书局内部一些人目为同仁刊物,由傅先生发起并亲自组稿编辑出版,投入大量心血。“1980年6月出初集,到现在已出版了十二集,……目前还有一集正在排印中,却已是拖了两年,迟迟未能印出,陷入经济危机。”印数也不断下降,特别是1988年,出现了大滑坡。傅先生就各集出版时间和印书作了统计:
初集1980年出,印了三万多册;二、三、四集1981年出,五、六集1982年出,七、八集1983年出,九集1984年出,印数都在一万几千册。1985年倒也出了两集(十、十一),印数已跌进一万以内了,而1985年以后,1986、1987两年都是空档,1988年1月才出了第十二集,印数只有二千五百册。这当然要亏本,出版部的同志不热心,经营管理的同志也提出意见。……有的开玩笑说:《学林漫录》的“漫”应该改为“慢”。
傅先生感叹:“前途如何,渺不可测,我们只求在排校中的第十三集还能印出来,希望苦撑一段时间,还能一集一集的编出来,哪怕慢一点。”(《〈学林漫录〉琐记》,《驼草集》812页)透着无奈和企望。
在回顾《唐才子传校笺》出版过程时,傅先生说:“第一册出版于1987年夏,等到第四册出版,已经是1990年的岁暮了,其间竟占了四个年头,我们现在出版一部稍具规模的学术著作,真有想不到的艰辛!”(《〈唐才子传校笺〉编余随札》,《驼草集》837页)
当他看到三联版陈寅恪《柳如是别传》首印一万册,不到一个月就销售一空时,开始关心报纸上的追问:“《柳如是别传》这一脱销现象,带给出版界一个什么启示?现在出版界都在谈论市场意识,那么什么是真正的市场?图书市场究竟需要什么?”(《〈柳如是别传〉怎样读》,《驼草集》1685页)傅先生的回答是:
不过我认为,图书市场的真正涵义是文化,一部有高品位文化的书,不但能带动图书市场,也还能使一个时期的图书市场有一种“更上一层楼”的活力。(同上1686页)
傅先生的愿望是真诚的,其目标指向是图书的文化含量和学术质量。面对出版界越来越强烈的追求经济效益的倾向,他明白“要改变过去单一产品经济模式,参加到商品经济的行列中去,因而重视经营中的经济效益,这不但无可厚非,而且也是应该的”。傅先生给出的出路——“我认为出路还在于我们自身”,一是自己要有一个信念,我们做的是文化积累的工作;二是“在竞争中力求高质量”,他说,可以预计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出版竞争会是相当激烈的,“学术工作不得不参加到这个竞争的机制中去”(《吴汝煜〈唐五代人交往诗索引〉序》,《驼草集》563页)。这样的想法体现了傅先生对学术质量的一贯追求,也符合他一贯严于责己的性格。
傅先生对自己认为该做而没做到的事,抱有真诚的愧意。1985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曹道衡先生的《中古文学史论文集》,反映极佳。但多年后,傅先生接到曹先生告知,他应台湾文津出版社之请,拟将《续编》交台湾出版,请傅先生作序。傅先生说:“我很惭愧在我主笔政之际未能将道衡先生有关中古文学研究论文编成续集在中华书局出版。”(《曹道衡〈中古文学史论文集续编〉序》,《驼草集》985页)
在谈到书局的小刊物《书品》时,傅先生说:“出版社应有文化学术意识。在目前市场经济的情况下,出版社当然不能忘记经营,而且要着意把经营搞好。但出版物并非是纯粹的商品,也不能简单地说把出版社推向市场。特别是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那么文化与学术应当是出版社的灵魂。”(《〈书品〉,与作者读者沟通的桥梁》,《驼草集》1224页)惭愧的是,援用傅先生前段的话,《书品》就是在我“主笔政”的时候关张的,也让很多读者失望。那是因为后来书评文章发表的范围大大突破,我们也大力鼓励编辑到外面的媒体发表,扩大影响力。借此机会我希望我们的员工年度文选《春华集》能够保持出下去。
以上主要是说的傅先生对出版现状的焦虑,作为主中华笔政、有引领学术风向之志的傅先生,竟然有与我们同样焦虑,这是这次阅读才集中关注到的。意识到这一点,我才对傅先生文中屡屡写到的“信念”(对文化的信念,对出版的信念)有所理解。
傅璇琮先生手迹从大处看,作为出版家的傅先生,有更值得我们汲取借鉴的地方。比如,与他对学术研究特别重视学科建设一样,他始终用学术的目标来规划出版、设计选题,引入出版;对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学术出版结构,他都有非常独到深远的考量;他总结历史上占有地位的出版社,“不管当时是赚钱或赔钱,它们总有两大特点,一是出好书,一是出人才”;傅先生对学术和出版始终抱有乐观的憧憬,是非常值得我们追效的。傅先生入职出版业之初,就“天真地立下一个志愿:我要当一个好编辑,当一个有研究水平的专业编辑”(《驼草集》1365页)。对中华书局,傅先生说:“我始终对这个环境是有感情的。”(《驼草集》2288页)反过来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二十年光景,就是傅璇琮们“主笔政”的年代,今之视昔,诚然是中华书局一百一十年史上既出人又出书的最高光时段之一,我有幸在入职之初,在他们的领导下工作,读《驼草集》,更有所感。编辑出版他们的著作,一方面是向前辈们致敬,另一方面这也是书局历史的一部分。
傅先生一再说:“我总以为,一个学者的生活意义,就在于他在学术行列中为时间所认定的位置。”(《驼草集》1563页)最后我要说,《驼草集》十册按年编排,读起来,真有展开半个世纪唐代文学、中国古典学术历程之感,也有展开改革开放以来古籍学术出版历程之感。这是《傅璇琮文集》超越其学术自身的历史价值。
2023年4月14日急就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